
打開(kāi)哲學(xué)之門(mén),打開(kāi)思考之門(mén)
——好書(shū)推薦之《打開(kāi)》
語(yǔ)文組 劉照建 整理供稿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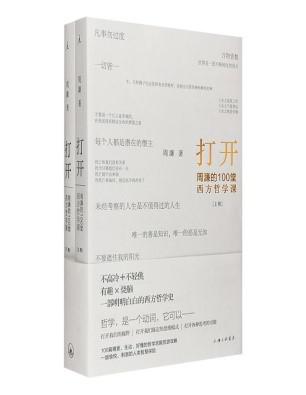
內(nèi)容介紹:
全書(shū)由一個(gè)個(gè)獨(dú)立的對(duì)哲學(xué)及哲學(xué)家們的趣味解讀組成。比如,康德是如何實(shí)現(xiàn)了既為人類的理性劃界,也為上帝和信仰留下地盤(pán)?為什么論起抽象和晦澀簡(jiǎn)直可以說(shuō)舉世無(wú)雙、獨(dú)孤求敗的黑格爾,卻批評(píng)我們普通人經(jīng)常陷入“抽象地思維”?兼有病態(tài)的人生和健康的哲學(xué)的尼采,為什么說(shuō)弱者、怨恨之人的靈魂是“歪”的?自由雅典與鐵血斯巴達(dá)共同之處在于——對(duì)“卓越”的不懈追求;提出“我思故我在”這個(gè)偉大命題的笛卡爾,居然是個(gè)賴床的哲學(xué)家;日常生活中“人畜無(wú)害”的胖子大衛(wèi)·休謨,在哲學(xué)領(lǐng)域卻是一個(gè)勇猛精進(jìn)的斗士;萊辛說(shuō)人們談?wù)撍官e諾莎就像談?wù)摗耙粭l死狗”,馬克思也說(shuō)哲學(xué)的老王黑格爾死后被當(dāng)成“一條死狗”,可是如今他們卻都死而不僵、借尸還魂了……縱觀西方哲學(xué)2500年的風(fēng)景,從古希臘到中世紀(jì),以至文藝復(fù)興、啟蒙運(yùn)動(dòng)和當(dāng)代,從泰勒斯、蘇格拉底、柏拉圖、到托馬斯·阿奎那、盧梭、康德、尼采、維特根斯坦、羅爾斯……哲人們的思想影響、改變了整個(gè)人類文明史,而具體到我們每一個(gè)個(gè)體來(lái)說(shuō),哲學(xué)有著不可言說(shuō)的慰藉與樂(lè)趣。
作者介紹:
周濂 1974年出生,先后獲北京大學(xué)哲學(xué)學(xué)士、碩士學(xué)位,香港中文大學(xué)哲學(xué)博士學(xué)位。2005年至今在中國(guó)人民大學(xué)哲學(xué)院任教,著有《現(xiàn)代政治的正當(dāng)性基礎(chǔ)》《你永遠(yuǎn)都無(wú)法叫醒一個(gè)裝睡的人》等。
讀者感悟:
哲學(xué)就是愛(ài)智慧
佚名
周濂說(shuō):“真正的哲學(xué)不是讓人免于思考,而是激發(fā)人們思考。”我覺(jué)得這本書(shū)對(duì)我來(lái)說(shuō)達(dá)到了書(shū)名的目的——《打開(kāi)》。在我看來(lái),這里的“打開(kāi)”有兩層含義,一是打開(kāi)哲學(xué)的大門(mén),一是打開(kāi)自己的大腦,開(kāi)始學(xué)著思考。
哲學(xué)的世界如一幅畫(huà)卷一樣在我面前徐徐展開(kāi),真的是絢麗多姿,精彩紛呈。
在哲學(xué)世界遨游的過(guò)程中,我的大腦也逐漸被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打開(kāi),有時(shí)候是一個(gè)看來(lái)很普通的問(wèn)題:好人真的能得到幸福嗎?我們比金魚(yú)看到的世界更真實(shí)嗎?
有時(shí)候是一句看似輕飄飄卻又深刻無(wú)比的話:“藝術(shù)家不必嚴(yán)肅認(rèn)真地反對(duì)官僚,這只會(huì)抬高他們的身價(jià),因?yàn)槟惴磳?duì)他們,說(shuō)明你把他們太當(dāng)回事,無(wú)意中反而加強(qiáng)了他們的權(quán)勢(shì),承認(rèn)了他們的權(quán)威。藝術(shù)家要把荒謬的東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即可。”
有時(shí)候是哲學(xué)家們之間互相矛盾的理論:康德之前的哲學(xué)家主張人類的“認(rèn)識(shí)符合對(duì)象”,康德反其道而行之,認(rèn)為應(yīng)該是“對(duì)象符合認(rèn)識(shí)”,這被稱為是“哥白尼式的革命”。
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撞擊著我的大腦,讓我一次次受到震撼,一次次懷疑世界,又一次次似乎被持不同觀點(diǎn)的哲學(xué)家們說(shuō)服。讀的過(guò)程中經(jīng)常感慨,原來(lái)我生活中面臨的那些問(wèn)題,哲學(xué)家也曾遇到過(guò),原來(lái)現(xiàn)實(shí)世界中的很多現(xiàn)象在哲學(xué)中都有對(duì)應(yīng)的理論解釋,原來(lái)當(dāng)今時(shí)代的很多問(wèn)題已經(jīng)被幾個(gè)世紀(jì)前的哲學(xué)家所預(yù)言。
讀完這本書(shū)我對(duì)哲學(xué)是什么依然沒(méi)有一個(gè)明確的概念,對(duì)每一位哲學(xué)家有什么主張也不能完全分辨清楚,但是有一種精神卻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腦海里,那就是對(duì)“未知”的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。
最早讓我看到這種精神的是洛克,他創(chuàng)作《人類理解論》的初衷,源自一次私人聚會(huì)。當(dāng)時(shí)有五六個(gè)朋友來(lái)他家里閑聊,談起一個(gè)話題,但很快就陷入僵局,于是大家停下來(lái)反思問(wèn)題到底出在哪里。在迷惑了很久之后,洛克提議,也許在討論這些問(wèn)題之前,應(yīng)該首先考察人的理解能力,看看哪些對(duì)象是人類的理解能力能夠解決的,哪些對(duì)象是人類的理解能力所不能解決的。洛克的提議得到大家響應(yīng)。于是,他開(kāi)始著手研究這個(gè)問(wèn)題,最終,在二十年后寫(xiě)出了這本《人類理解論》。
作者說(shuō):“在一次私人聚會(huì)的閑談中,從一個(gè)毫不相干的問(wèn)題出發(fā),因?yàn)榘偎疾坏闷浣猓詻Q定刨根問(wèn)底,轉(zhuǎn)而探討人類理解這樣的根本問(wèn)題,并且一探討就是二十年,每當(dāng)我讀到這個(gè)段落時(shí),都無(wú)比嘆服于西方哲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。”
這個(gè)事例對(duì)我的打動(dòng)不亞于周濂老師心中的嘆服,哲學(xué)家們這種對(duì)問(wèn)題的執(zhí)著與堅(jiān)持,著實(shí)令人嘆服。我們普通人遇到這樣的事情大多會(huì)放棄,想不通的問(wèn)題那就不想了唄,又不影響生活,干嘛自尋煩惱呢?我們很難用一生的時(shí)間與精力去時(shí)時(shí)想著那個(gè)最開(kāi)始困擾我們的問(wèn)題,更不要說(shuō)最后還能寫(xiě)出一本書(shū),給出自己的一個(gè)思考。
這種打動(dòng)人心的求知欲貫穿了整部哲學(xué)史,是刻在每一位哲學(xué)家骨子里的精神,我想也是刻在所有人類基因中的精神,正是這種對(duì)知識(shí)永不停歇的探索與追求,才推動(dòng)了哲學(xué)的發(fā)展,推動(dòng)了世界的進(jìn)步,推動(dòng)了人類的成長(zhǎng)。或許這正是哲學(xué)的本質(zhì),就如作者在一開(kāi)始解釋“哲學(xué)是什么”這個(gè)問(wèn)題時(shí)所給出的定義:哲學(xué)就是愛(ài)智慧。